在前人译有《飞鸟集》之后,后来的多种中译本,包括大胆的冯唐译本,都规矩地沿用这个书名。可傅浩的《失群之鸟》却乱了队形。不同的译法迫使读者回到原文。泰戈尔的诗集原名“Stray Birds”(“stray”作形容词时义为“离群走失的”),“飞”明显是译者所为。既然真相这样简单,而且原文本不复杂,为什么至少十种中译本都没有照实翻译,而是沿用“飞鸟集”?译者们是真心认可这个译法,还是为了“致敬经典”?或是有别的考虑?无论如何,他们的选择至少表明一点:没有把原作放在第一位。
原作却总是傅浩的首要依据,他主张“直译为常”,以“不增不减”“字字有着落”为愿。在其近作《叶芝诗解》(英文书名的汉译是《叶芝诗选译解》,以下简称《诗解》)的绪论中,他说“最好的译本和解说都是尊重作者本意的,而不是任意发挥的”。原作和作者至上的理念,以及在译解实践中落实这种理念的能力,让人想到另一位同样身兼学者(教授)、诗人(作家)、译者等身份的译注者——纳博科夫。

《叶芝诗解》
傅浩著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48.00元
ISBN:978-7-5446-6759-3
《诗解》选取爱尔兰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的89首英语诗作为译解对象,在每首诗的汉语译文与诗解之前放上诗作原文。译文以直译为常,力求在词义、句式、节奏与韵律、文体等各方面都紧贴原文;解说则是对原作具体、细致的“CT扫描”,包括如追踪作品的创作过程、解释文本的文字意思、阐明诗人的文学理念和形而上思想、通过文字或图像展示与作品相关的重要场景等内容。做过这样通透的解说,译文还有多少机会出错?
“在一部诗作的注释中说一通一般观念,就等于在文本翻译中进行意译。面前的著作这两种笼统现象都不存在。”这是纳博科夫在上个世纪为其译注的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草拟的一则腰封简介,用于《诗解》也似无不妥。
叶芝“Long-legged Fly”一诗的题名,曾被译作“长脚蚊”、“长腿蜻蛉”。傅浩的译法则是“长足虻”。他在诗解中告诉读者:“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长足虻是一种双翅目长足虻科昆虫。形小,蓝或绿色,有金属光泽。捕食较小的昆虫,见于隐湿的沼泽周围”,“这种昆虫具有踏水而行的能力。”这种认真,有点像讲《变形记》时的纳博科夫,他提醒学生注意,格里高尔变成的那只昆虫是甲虫而非某些注者或译者所说的蟑螂或屎壳郎。一个词如果被误认作另一个“差不多”的词,对文本大局似乎不会造成严重影响,但对于希望如实见到作者所想、感受艺术细节的读者来说,就不是一件小事了。所幸傅浩的译文(下简称傅译)总能让人看见真实。
而一些不实不确的译法或说法,也被《诗解》指出。《湖岛因尼斯弗里》的因尼斯弗里(Innisfree),并非某些评论者所说的“inner’s free”(内在的自由),该词是盖尔语,义为“石楠岛”,是叶芝家乡一个真实的湖岛;《在你年老时》里大写的“Love”尽管总被译成“爱”或“爱情”,但它其实是个拟人化的概念,指爱神,结合下文“his”来看,是指爱神维纳斯之子即小爱神丘比特,叶芝的另一首诗也可佐证这一结论;《布尔本山下》“把人类的灵魂引向上帝,/让他把摇篮填充得恰当”这句,并不像1990年伦敦版《叶芝诗集》的编者所说,指诗人相信艺术作品能够对胎儿发育产生影响,理解此词应结合诗人的神秘哲学体系,“摇篮在叶芝的象征体系中是月相的别称,…… ‘把摇篮填充得恰当’意思是说在正确的月相下投生,则生而具有相应的人格。”
真实,或尽可能多的真实,是《诗解》作者的追求,在他那里,甚至诗人自己的解说也未必总是终极答案。按诗人自注,《白鸟》的“白鸟”是传说中仙境里白如雪的鸟,但《诗解》作者未止步于此。他根据更多资料,还有自己在诗人写作此诗前几日所到之处的亲眼所见——“荒凉的高崖下别无他物,只有大群的海鸥在海面上盘旋觅食”,判断此诗诞生的三天之前诗人与自己的意中人在厚斯崖所见的海鸥,是此诗的灵感来源,当时,一对海鸥掠过头顶,飞向海面,意中人说,假如再生为鸟,会选择海鸥(《白鸟》第一句即“我情愿我们是,亲爱的,浪花之上一双白鸟”)。这种判断合情合理。
谈纳博科夫译注的《叶甫盖尼·奥涅金》时,纳博科夫的传记作者说他“不断抛弃广为接受的意见和熟悉的事实”、“兀兀穷年,旁搜远绍,不放过任何一个能发现的原始材料”。这些评价好像也适用于《诗解》作者。
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诗解》作者研究叶芝已有四十年。多年积累的材料,不仅助他正确理解字词的意思,也助他正确把握诗作的整体风格,从而选取相应的译法。《经那些柳园往下去》就是一例。此诗是诗人根据“在斯来沟采集的三行歌词——爱尔兰老歌词——所作”,“采用的是谣曲形式,即奇数行四个音步,偶数行三个音步交错排列的诗节。只不过排印采取了把奇偶两行连排成一行的形式。”傅译“以顿代步”的处理(即在此诗奇数行设置三个语意停顿、偶数行设置两个语意停顿,以对应原文奇数行四个音步、偶数行三个音步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译文与原作节奏的一致。摘第一节译文如下:
经|那些|柳园|往下去,爱人|和我|曾会面;
用|一双|雪白的|小脚,她走过|那些|柳园。
她|教我|从容|看爱情,一如|枝头|生绿叶,
可是|我|年少|又愚蠢,不同意|她的|见解。
译文用词偏口语,也符合谣曲的特点。相比之下,虽然另一位译者似乎也注意到原作奇偶行的划分,而且译文(摘第一节如下:“黄柳园畔,我和爱人相遇;/她纤足雪白,走过柳园。/她劝我从容相爱,如叶生树梢;/可我年轻糊涂,未听她劝告”)若只从汉语角度看,甚至好像比傅译更简洁典雅,但正是偏书面的遣词造句,以及个别错译和漏译,造成译文与原作在意思和风格上不完全相符,终归有失忠信。傅译不仅在语义、节奏、风格上忠于原作,原作的毗邻韵即aabb韵式,在傅译中也得到展现。不唯此例,傅浩译诗时总是尽量按照原诗韵式押韵,而在原诗不押韵处,译文也不画蛇添足。大概这就是“不增不减”的一种体现。
由上可见,学者傅浩的博学与慎思,让他的翻译和解说有更多贴近原作与作者本意的可能。同时,诗人傅浩对语言的敏感,也是保证其译文质量的重要原因。他清楚“His”不是“his”,因此译作“祂”而非“他”;知道“Chinamen”和“Chinese”不同,因此译作“中国佬”而非“中国人”;他大概还会从“茉”里看到白色花朵,因此用它而非“莫”来翻译一位如花美眷的名字。
诗人与学者的素养,让译者在翻译时如虎添翼,往往能产出更加精确的译文。不过,并非每位既是诗人又是学者的译者都能做到精确或正确,具体情况因人而异,译文可信的首要前提还是译者的发心,即是否决心以作者本意为依。
是否决心以作者本意为依,这原本不该成为问题。但事实却是,有违作者本意的情况屡见不鲜。正因如此,固执原文真相、尊重作者本意的译解者尤其可贵。即使原作作者通常无力反抗,即使不是每位读者都会逐行比对译文与原文,即使一般读者对原作作者可能了解不多,即使译文和解文的准确度大多时候只有自己知道,理想的译解者也同样不会马虎,更不会任意发挥。这就是古人的“君子慎独”“敬以直内”“庸言之信”,也类似叶芝的“灵魂的至诚”——对自己,对缪斯,对天地,正如《诗解》作者的自白——“修辞以立诚,这就近乎修行,由技而入道了”。
(本文原载于《中华读书报》
2022年6月8日,发表时有删节)

发布者:管理团队,转转请注明出处:https://lib.ecolearning.cn/archives/215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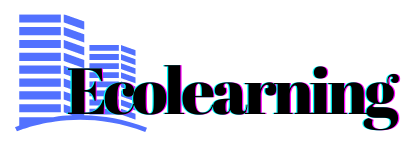
 微信扫一扫
微信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
支付宝扫一扫